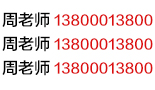热点新闻
联系方式
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
培训一部:0539—8025001
培训二部:0539—8025001
培训三部:0539—8025001
培训四部:0539—8025001
后 勤 部:0539—8025001
网络宣传:0539—8025001
邮箱: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临沂市文化中心14楼
沂蒙精神
论中央苏区妇女对农业生产的贡献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次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特殊环境下,中央苏区广大妇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苏区妇女获得了土地和解放后,迸发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农业生产事业,为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也赢得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承认和尊重。
一、中央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动因
(一)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根据地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客观需要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蒋介石严禁军用品、盐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输入根据地,并规定对私运商品的商人处以极刑。在白区还设立“公卖会”,在赤白交界处设立“封锁卡”,封锁商品出入,同时搜刮群众的粮食汇集到自己的堡垒中。在严酷的经济封锁环境下,中央根据地军民在开展反军事“围剿”的同时,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尤其是大力开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1]农业摆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首位的思想,反映了当时苏区的客观需求。由于国民党军的烧杀抢掠,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人口数量下降,同时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根据地农业生产存在着劳动力不足、耕牛不足、生产工具匮乏和资金不足等困难。其中劳动力不足成为阻碍农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写道:“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 人,当红军做工作的 485 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 756 人,当红军做工作的 526 人,占 70%。”在苏区大部分革命根据地中,都存在着类似才溪县这样的情况。留守根据地的,主要是老弱妇残,他们分得了土地,没有劳动力耕种,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很好地利用。在根据地人口组成中,妇女人数众多,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潜在伟力,《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妇女运动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8日) 指出:“占人口半数的闽西妇女群众在生产上与男人同样重要。妇女占人口之半数,……妇女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如果妇女不起来,则暴动后男子征调入伍,社会生产也会发生问题。”中央苏区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和发动苏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客观需求更是呼唤苏区妇女充分发掘蕴藏着的伟大力量。
(二)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自我解放后觉悟的充分表达
传统中国女性丧失“人”的独立与尊严,政治上不能参与政事、国事,经济上没有独立职业、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女子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她们只能依附于男人而生存。婚姻上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只能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惟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教育上,古人认为女性不宜识字,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当时赣南、闽西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古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我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才溪乡有一个村的族长规定在家祠演戏,要用竹篱笆将男女隔开。有一次,一名妇女进入男人们的地盘看戏,便被族长吊起来示众。在才溪乡下才溪村,有位妇女上圩场时,路上与一位男子前后走的相隔不到 10 米远,便被地主豪绅认为是伤风败俗,竟被活活打死。广大妇女们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毛泽东曾在中央苏区进行深入的调查,指出:在土地革命以前,赣南、闽西的广大农村妇女,“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生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虽然犁田、耙田、挑米等工作多由男子担任,但是大多妇女也承担一定的重活。除了要帮忙农事,还从事烧茶煮饭、经营头牲、挑水养猪、补衣做鞋等家庭事务,妇女们还须养育儿女。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目睹了妇女们所处的困境:“她们是男子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
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后,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妇女解放。苏区妇女们渐渐在政治、经济、婚姻、教育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尤其是在经济上,她们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在经济上实现了男女平等,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认识到如果她们参与到革命中去,就可以改变自己没有人身自由的现状,因而表现出炽热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拥护革命,支持革命,同时也亲身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去。
二、中央苏区政府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与措施
(一)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
中央苏区政府为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妇女深刻认识参加农业生产与妇女解放的密切关系,鼓励妇女走出家门。毛泽东从 1930 年至 1933 年间,先后在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的吉安、寻乌、兴国、长冈及福建的才溪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邀请妇女干部和群众参加调查会,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1932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关于维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中明确提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方面女子不能独立,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发展、参加生产劳动是实现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指出:“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他还提出:“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是最积极的革命参加者,而应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组织中来。”[2](P16)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清晰说明了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和革命的关系:“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妇女占劳动群众的半数,劳动妇女积极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对于革命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日益扩大的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中,多数男子均要到红军里去参加前线工作,则后方的工作与巩固、保卫的责任更多由妇女来担当,坚决实现保护与解放妇女的法令,领导与激励劳动妇女来积极参加革命,使与妇女运动密切联系起来,以增加革命胜利的建设。”[3](P60)要求“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已的日程上”。[4](P314)
通过调查访问和广泛宣传,广大苏区妇女的觉悟程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动员和组织了许多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二)发布法令法规,使妇女享有政治经济权利
婚姻问题是事关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为改变旧社会对妇女婚姻制度的束缚,发动广大苏区妇女投入到革命中,1931 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婚姻条例》,这个条例体现了 3 项重要的原则。一是强调“婚姻以自由为原则”,二是一夫一妻制原则,三是保护妇女权益的原则。苏维埃政府还颁布了《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年满 16 岁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1年,《中央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妇女亦与男子一样,有独立支配自己所分配得来的土地的自由——她的土地或与父母兄弟共耕,或自己单独耕种都可以,依她自由意志决定。”[2](P17)1933 年苏区中央政府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指出“加入互助社者以家为单位”“,凡是农民(贫农中农)、农民工人及其他有选举权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可加入”。中央政府在 1933 年 3 月和 4 月相继颁布了《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和《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界定所有权问题:“耕牛和农具是全体站员所公有,新生的牛仔也归站员所有”,[5]妇女们作为犁牛合作社的成员,拥有使用耕牛和农具的权利。
苏区政府一方面在法规法令上保障妇女获得与男性的平等权益,特别是参政权和土地分配权。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实施层面鼓励妇女参与政府管理。在江西长冈乡西逸亭村政府办事处有5 人,包括主席、秘书、粮食委员、土地委员、妇女委员。在长冈乡“女工农妇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4](P312)上杭才溪乡的“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的主任。”[6](P329)
这些政令与举措使苏区妇女在社会上第一次享受到做人的权利,获得了土地,获得了独立人格的广大翻身苏区妇女,迸发出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扩红、支前、生产中,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土地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建立各级妇女组织和农业组织,领导和吸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毛泽东、刘少奇曾精辟地论述了组织的重要性:“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7]“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要纽带”。[8]的确,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认为,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来指导。因此,中央苏区政府建立了各级妇女组织,党和政府里设置了妇女部(或称妇委),负责领导妇女工作,之后还设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宗旨是:为使劳动妇女能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权力,消灭封建旧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使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经常深入调查妇女生活,并且具体计划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开展有效工作,成为政府与广大妇女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成立妇女单独的组织——农工农妇代表会,目的是对妇女进行文化教育,吸收女工农妇参加苏维埃建设。此外,还在特区、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成立劳动妇女的群众性组织——妇女会,建立和健全了妇女运动的各级组织机构。
此外,在各乡还成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指导广大的妇女群众犁田耙田等主要的生产工作,全区80%的妇女都学会了犁田、耙田。上杭县还组织了77 个妇女生产教育组,10 人为 1 小组,1 组有 3 个老农为教员,各小组每天半日轮流学习主要的生产劳动。
中央苏区政府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既解决农业生产上劳力、耕畜、农具不足的困难,又能发挥集体劳动的协作精神,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后指出:“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劳动。”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妇女成群结队地参加生产,是一次广泛的群众运动。长冈乡当时的农业生产不减少,反而增加了。长冈乡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到江西全省苏区,当时江西全省迅速形成了妇女犁田耙田的高潮,后来人们称中央苏区妇女为“不怕雷公打”的英雄。
三、中央苏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一)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表现突出
妇女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力量,苏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春耕时,她们组织耕田队、开荒队,犁田、耙田、下料、换种、开垦荒地、修池塘、筑河坝,“永远是那样紧张,没有丝毫的疲倦”。1934年,虽然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形势严峻,中央苏区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如闽浙赣省平均每亩田收谷1 担,比前年增加了一担,油菜比革命前增加一倍,棉花足以自给,不用到白区去买,开荒 3 万多亩,增加几十万担米谷,修成水路 602条,石坝 230 支,山塘 750 口。整个苏区的秋收,平均增加了一成半。农业取得巨大丰收,与广大苏区妇女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
苏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参与面广,同时在劳动过程争当生产能手。1934 年的春耕和秋收运动中,兴国妇女参加主要生产事业的有 2 万以上,学好犁田耙田的8千以上,能耕种割禾等附带劳动的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红色中国》是这样报道才溪劳动妇女春耕的:“……生产上,由于妇女们的努力,才溪1933 年粮食生产比 1932 年增加了 50%”。1933 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组织的春耕检阅中,高度称赞才溪是“最特色的模范区”,“尤其令人钦佩和称赞的,才溪的妇女真是一支有力的产业军”。她们满怀革命激情,经常在田野中唱着解放的山歌:“劳动妇女学犁田,英勇哥哥前方去,后方生产妹承担”。当时根据地流传着一首民歌:“革命红旗迎风扬,妇女耕田又开荒,志愿红军打败仗,多收粮食送前方。”1933 年中央苏区开展了以春耕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生产竞赛,其中涌现出许多生产能手和妇女模范。如长冈乡妇女主任、耕田队长李玉英受到了毛泽覃的表扬,中央临时政府还专门奖励她一条有镰刀斧头的蓝色围裙。当时身兼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的蔡畅在宁都请老农传授技术,学会了犁田、耙田和插秧等各种农活,她还把各乡妇女代表集中起来分批轮训。[4](P315)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妇女所起的作用做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 “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9]“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维埃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姿与伟大成绩。”[4]
(二)展现妇女的伟大力量,实现妇女解放与革命的互动
传统中国女性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地位低下,生活艰苦。苏区妇女们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参与到农业生产,取得了经济独立,婚姻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妇女参与政权管理,男女平权思想变成了社会现实。妇女们在农业生产上,彰显了女性的能力,她们在生产上的突出贡献证明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观念的错误,广大苏区妇女在反对封建压迫、谋求自身解放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妇女解放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劳动成为唤起妇女阶级意识的觉醒,实现妇女性别解放和阶级、社会解放的现实途径。妇女开始冲破传统性别角色的禁锢,走向社会,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所言:“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这种变化对于从前自我意识甚少的农村妇女是空前的,她们将自己的命运同红军和根据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保卫根据地,展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在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中,推动了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实现了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 193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江西省妇联,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A].毛泽东文集(第 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互助社纲要[Z].1933 年 3 月.
[6]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A].毛泽东文集(第 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刘少奇选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A].毛泽东文集(第 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一、中央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动因
(一)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根据地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客观需要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蒋介石严禁军用品、盐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输入根据地,并规定对私运商品的商人处以极刑。在白区还设立“公卖会”,在赤白交界处设立“封锁卡”,封锁商品出入,同时搜刮群众的粮食汇集到自己的堡垒中。在严酷的经济封锁环境下,中央根据地军民在开展反军事“围剿”的同时,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尤其是大力开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1]农业摆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首位的思想,反映了当时苏区的客观需求。由于国民党军的烧杀抢掠,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人口数量下降,同时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根据地农业生产存在着劳动力不足、耕牛不足、生产工具匮乏和资金不足等困难。其中劳动力不足成为阻碍农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写道:“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 人,当红军做工作的 485 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 756 人,当红军做工作的 526 人,占 70%。”在苏区大部分革命根据地中,都存在着类似才溪县这样的情况。留守根据地的,主要是老弱妇残,他们分得了土地,没有劳动力耕种,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很好地利用。在根据地人口组成中,妇女人数众多,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潜在伟力,《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妇女运动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8日) 指出:“占人口半数的闽西妇女群众在生产上与男人同样重要。妇女占人口之半数,……妇女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如果妇女不起来,则暴动后男子征调入伍,社会生产也会发生问题。”中央苏区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和发动苏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客观需求更是呼唤苏区妇女充分发掘蕴藏着的伟大力量。
(二)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自我解放后觉悟的充分表达
传统中国女性丧失“人”的独立与尊严,政治上不能参与政事、国事,经济上没有独立职业、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女子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她们只能依附于男人而生存。婚姻上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只能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惟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教育上,古人认为女性不宜识字,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当时赣南、闽西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古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我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才溪乡有一个村的族长规定在家祠演戏,要用竹篱笆将男女隔开。有一次,一名妇女进入男人们的地盘看戏,便被族长吊起来示众。在才溪乡下才溪村,有位妇女上圩场时,路上与一位男子前后走的相隔不到 10 米远,便被地主豪绅认为是伤风败俗,竟被活活打死。广大妇女们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毛泽东曾在中央苏区进行深入的调查,指出:在土地革命以前,赣南、闽西的广大农村妇女,“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生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虽然犁田、耙田、挑米等工作多由男子担任,但是大多妇女也承担一定的重活。除了要帮忙农事,还从事烧茶煮饭、经营头牲、挑水养猪、补衣做鞋等家庭事务,妇女们还须养育儿女。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目睹了妇女们所处的困境:“她们是男子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
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后,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妇女解放。苏区妇女们渐渐在政治、经济、婚姻、教育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尤其是在经济上,她们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在经济上实现了男女平等,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认识到如果她们参与到革命中去,就可以改变自己没有人身自由的现状,因而表现出炽热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拥护革命,支持革命,同时也亲身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去。
二、中央苏区政府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与措施
(一)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
中央苏区政府为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妇女深刻认识参加农业生产与妇女解放的密切关系,鼓励妇女走出家门。毛泽东从 1930 年至 1933 年间,先后在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的吉安、寻乌、兴国、长冈及福建的才溪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邀请妇女干部和群众参加调查会,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1932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关于维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中明确提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方面女子不能独立,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发展、参加生产劳动是实现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指出:“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他还提出:“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是最积极的革命参加者,而应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组织中来。”[2](P16)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清晰说明了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和革命的关系:“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妇女占劳动群众的半数,劳动妇女积极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对于革命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日益扩大的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中,多数男子均要到红军里去参加前线工作,则后方的工作与巩固、保卫的责任更多由妇女来担当,坚决实现保护与解放妇女的法令,领导与激励劳动妇女来积极参加革命,使与妇女运动密切联系起来,以增加革命胜利的建设。”[3](P60)要求“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已的日程上”。[4](P314)
通过调查访问和广泛宣传,广大苏区妇女的觉悟程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动员和组织了许多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二)发布法令法规,使妇女享有政治经济权利
婚姻问题是事关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为改变旧社会对妇女婚姻制度的束缚,发动广大苏区妇女投入到革命中,1931 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婚姻条例》,这个条例体现了 3 项重要的原则。一是强调“婚姻以自由为原则”,二是一夫一妻制原则,三是保护妇女权益的原则。苏维埃政府还颁布了《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年满 16 岁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1年,《中央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妇女亦与男子一样,有独立支配自己所分配得来的土地的自由——她的土地或与父母兄弟共耕,或自己单独耕种都可以,依她自由意志决定。”[2](P17)1933 年苏区中央政府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指出“加入互助社者以家为单位”“,凡是农民(贫农中农)、农民工人及其他有选举权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可加入”。中央政府在 1933 年 3 月和 4 月相继颁布了《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和《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界定所有权问题:“耕牛和农具是全体站员所公有,新生的牛仔也归站员所有”,[5]妇女们作为犁牛合作社的成员,拥有使用耕牛和农具的权利。
苏区政府一方面在法规法令上保障妇女获得与男性的平等权益,特别是参政权和土地分配权。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实施层面鼓励妇女参与政府管理。在江西长冈乡西逸亭村政府办事处有5 人,包括主席、秘书、粮食委员、土地委员、妇女委员。在长冈乡“女工农妇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4](P312)上杭才溪乡的“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的主任。”[6](P329)
这些政令与举措使苏区妇女在社会上第一次享受到做人的权利,获得了土地,获得了独立人格的广大翻身苏区妇女,迸发出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扩红、支前、生产中,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土地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建立各级妇女组织和农业组织,领导和吸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毛泽东、刘少奇曾精辟地论述了组织的重要性:“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7]“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要纽带”。[8]的确,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认为,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来指导。因此,中央苏区政府建立了各级妇女组织,党和政府里设置了妇女部(或称妇委),负责领导妇女工作,之后还设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宗旨是:为使劳动妇女能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权力,消灭封建旧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使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经常深入调查妇女生活,并且具体计划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开展有效工作,成为政府与广大妇女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成立妇女单独的组织——农工农妇代表会,目的是对妇女进行文化教育,吸收女工农妇参加苏维埃建设。此外,还在特区、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成立劳动妇女的群众性组织——妇女会,建立和健全了妇女运动的各级组织机构。
此外,在各乡还成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指导广大的妇女群众犁田耙田等主要的生产工作,全区80%的妇女都学会了犁田、耙田。上杭县还组织了77 个妇女生产教育组,10 人为 1 小组,1 组有 3 个老农为教员,各小组每天半日轮流学习主要的生产劳动。
中央苏区政府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既解决农业生产上劳力、耕畜、农具不足的困难,又能发挥集体劳动的协作精神,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后指出:“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劳动。”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妇女成群结队地参加生产,是一次广泛的群众运动。长冈乡当时的农业生产不减少,反而增加了。长冈乡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到江西全省苏区,当时江西全省迅速形成了妇女犁田耙田的高潮,后来人们称中央苏区妇女为“不怕雷公打”的英雄。
三、中央苏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一)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表现突出
妇女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力量,苏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春耕时,她们组织耕田队、开荒队,犁田、耙田、下料、换种、开垦荒地、修池塘、筑河坝,“永远是那样紧张,没有丝毫的疲倦”。1934年,虽然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形势严峻,中央苏区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如闽浙赣省平均每亩田收谷1 担,比前年增加了一担,油菜比革命前增加一倍,棉花足以自给,不用到白区去买,开荒 3 万多亩,增加几十万担米谷,修成水路 602条,石坝 230 支,山塘 750 口。整个苏区的秋收,平均增加了一成半。农业取得巨大丰收,与广大苏区妇女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
苏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参与面广,同时在劳动过程争当生产能手。1934 年的春耕和秋收运动中,兴国妇女参加主要生产事业的有 2 万以上,学好犁田耙田的8千以上,能耕种割禾等附带劳动的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红色中国》是这样报道才溪劳动妇女春耕的:“……生产上,由于妇女们的努力,才溪1933 年粮食生产比 1932 年增加了 50%”。1933 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组织的春耕检阅中,高度称赞才溪是“最特色的模范区”,“尤其令人钦佩和称赞的,才溪的妇女真是一支有力的产业军”。她们满怀革命激情,经常在田野中唱着解放的山歌:“劳动妇女学犁田,英勇哥哥前方去,后方生产妹承担”。当时根据地流传着一首民歌:“革命红旗迎风扬,妇女耕田又开荒,志愿红军打败仗,多收粮食送前方。”1933 年中央苏区开展了以春耕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生产竞赛,其中涌现出许多生产能手和妇女模范。如长冈乡妇女主任、耕田队长李玉英受到了毛泽覃的表扬,中央临时政府还专门奖励她一条有镰刀斧头的蓝色围裙。当时身兼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的蔡畅在宁都请老农传授技术,学会了犁田、耙田和插秧等各种农活,她还把各乡妇女代表集中起来分批轮训。[4](P315)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妇女所起的作用做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 “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9]“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维埃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姿与伟大成绩。”[4]
(二)展现妇女的伟大力量,实现妇女解放与革命的互动
传统中国女性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地位低下,生活艰苦。苏区妇女们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参与到农业生产,取得了经济独立,婚姻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妇女参与政权管理,男女平权思想变成了社会现实。妇女们在农业生产上,彰显了女性的能力,她们在生产上的突出贡献证明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观念的错误,广大苏区妇女在反对封建压迫、谋求自身解放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妇女解放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劳动成为唤起妇女阶级意识的觉醒,实现妇女性别解放和阶级、社会解放的现实途径。妇女开始冲破传统性别角色的禁锢,走向社会,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所言:“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这种变化对于从前自我意识甚少的农村妇女是空前的,她们将自己的命运同红军和根据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保卫根据地,展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在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中,推动了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实现了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 193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江西省妇联,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A].毛泽东文集(第 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互助社纲要[Z].1933 年 3 月.
[6]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A].毛泽东文集(第 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刘少奇选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A].毛泽东文集(第 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